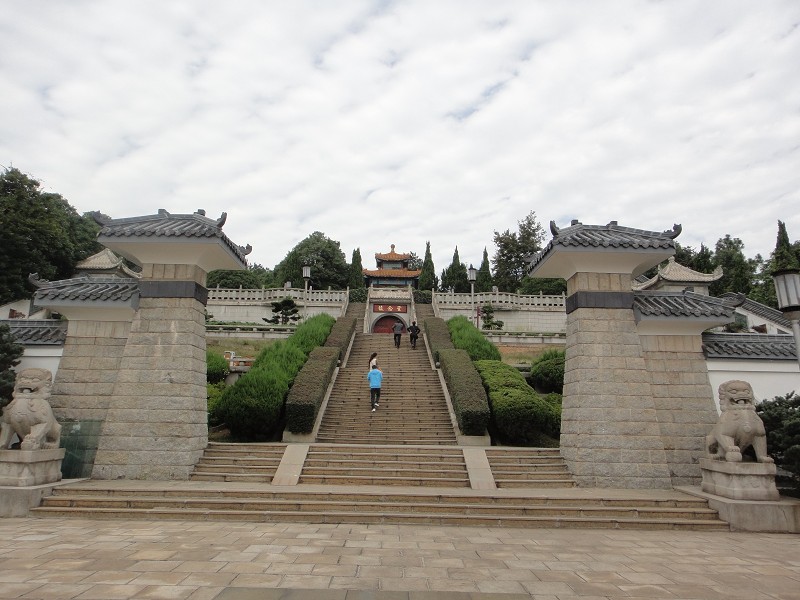儿时坐火车,爸爸告诉火车上有煮饭的车厢,有不用蒸子蒸饭的大烘箱,有用电炒菜的大炒锅。我很新奇,想去看、想去吃,人太多,爸爸带着我挤不过去。工作后坐火车,想去了却儿时的嘴馋,又碍于囊中羞涩,夜晚肚子饿得咕咕叫,站在餐车门前盯着那些文明人举起红酒杯慢慢品酒的假斯文,想着有朝一日定来餐车海吃一顿,解馋解闷解囊中羞涩的卑微。后来有钱了,坐火车把自己关进了卧铺车厢里,嫌去餐车太挤,怕身上的钱袋子在人群中溜进了别人的腰包里,死死地守着一层叠一层腰杆也直不起的窝。
前不久,外出回家。途中买了张22:00点启程无座的火车票,我很纠结,要在火车上站十四个小时。我恨“无座”二字,明明是站票,硬是要变着法在票面子打上“座”的字样,分明是在忽弄不会咬文弄字的乡巴佬。
夜幕降临,怀化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头蠕动、灯火辉煌。荧屏显示牌上显示出长沙开往成都的火车晚点1:49分。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有一种好的感觉,在大厅里坐着肯定比在火车上站着好受。大厅里的广播响起,反复播出一位爹声爹气的女音:“亲亲我的同志,从长沙开往成都的火车晚点一小时四十九分,我代表全体列车员向你表示歉意。”我全身突然冒起鸡皮疙瘩。连国家主席也称友好之邦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讲话也称女士们先生们。突然感到“同志”的称呼落伍了太别扭,“亲亲我”又前卫了太大胆。要是全厅的人都把她的话当了真,去亲亲她,那张脸不去医院整容才是怪事!
身旁一位吉首大学的“胖墩”也无座,他不以为然,是这条道上的常客,有着丰富的赶火车经验。他告诉我,上车后就混到卧铺车厢去睡觉,查票被撵出来再去。老大不小了,在社会上混了一辈子也没学到这本事,怕被查出来丢面子,做这种不光彩的事实在缺乏勇气。他又说可以去餐车坐,缴三十元钱就行了。这倒是好消息,可是这么多人无座,小小的餐车可能早已坐满,但也给我残存下一线希望。想着过去赶火车,夜晚像贼一样钻到座位下打发时光躺瞌睡,真不是人受的。旁边的一位女子为自己有一张座票而开心,好心地邀我在车上换着坐,让我有些感激。
晚点的火车24:00点到站,人们蜂拥而去。我最后一个懒懒地从大厅座椅上抬起屁股,回头对空出的座椅有些贪恋。不慌不忙走在最后,反正上了火车都是站。进到站台,见列车后面的卧铺车厢里黑黢黢,前面的硬座车厢灯火昏暗,只有第八节餐车灯火通明。手里拿着票,没去票上指定的第一节车厢,直径去了第八节餐车。直杠杠地告诉站在车门检票的列车员,无座,想去餐车买个座位。列车员望着我,些许见我老实不会干出见不得人的勾当,些许见我头发花白起了怜悯之心,让我上了车。吉首大学的胖墩跟在后面对列车员说我们是一起的,也上了车。
餐车门紧锁。里面坐着几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和白衣的厨子,莫不是餐车不提供座位了,沮丧起来。轻轻地拍打餐车门,一位厨子虚开门缝问:“做什么?”
“想补钱找个座位。”
厨子把我们放了进去。我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原来一切担心都是多余。
火车悄然离开了站台,紧接着车厢连接处哐嘡一声碰撞,然后哐嘡声一阵紧一阵传下去,接着就开始了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
餐车门前站着背包的男子、抱孩的妇人、抽烟的大汉、拖箱的妹子,都和我当年一样碍于囊中羞涩,不敢进餐车。时髦的有钱的活在当下开心享乐的壮着胆子走了进来。一位身穿沾满油污的白衣厨子说话有些结巴,坐在餐车硬座一侧把着门,问一对进门的年轻人:“去……去哪里?”
“去卧铺车厢。”
“票……票呢?”
“没有。我们补票。”
“没卧铺了。出去!出去!”
一会,一位小伙子抱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进来。“去哪里?”
白衣结巴厨子问。
“吃饭。”
“下班了。没饭菜了。只有盒饭。”
“盒饭也可以。”小伙子牵着小孩进到餐车,坐在进门的第一个座位。小伙眉目清秀、衣作整洁很斯文,小孩也惹人爱。孩子没有一点食欲,把饭当菜,一颗饭一颗饭夹着吃,不一会就睡着了。盒饭放在餐桌上,小伙子把孩子放在座椅上,孩子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静静地坐着,没有吃剩下的盒饭。我想盒饭就这样扔了多可惜。
购卧铺的那对年轻人又进来了,主动对白衣厨子说:“找个座位。”
“要补钱?”
“可以。”年轻人经过刚才去卧铺车厢的试探,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很爽快地应允了,坐在了我前面。
这对年轻人看上去是在路途相识的,有些相见恨晚,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穿着时髦精灵的小女子对身穿西装稳重的男子十分崇拜,有问不完的问题。男子像行走江湖的郎中,对女子的提问回答很得体。
与我同上车的吉首大学的胖墩趁餐车中的列车员去检查,溜进了卧铺车厢,回头向我自豪地挥挥手,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不一会,他又灰溜溜回来了,一位穿制服的列车员走在他后面。
此时,餐车上已经有了十来个人。白衣结巴厨子来到座位前,开始收钱。年轻人问:“多少钱?”
“一位三十五。”
“不是三十吗?”女子问。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一会给你们一人一瓶水和一盒糕点。”
女子争着付钱,男子也争着付钱,结果AA制。我好笑,都是提劲绷面子,假打!
我爽快地付了钱,心踏实下来,精神不再受到担惊站着乘车的侵扰,很是满足。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车厢都挤爆了,行李架上、座椅下、厕所里都是人,宁肯让餐车空着也不让进去。那时候乘车的人太老实,列车上的管理者太机械,都没想出收钱这一招。真有点感激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方便。
白衣结巴厨子来到带小孩的小伙子身边。小孩已经熟睡。男子早已有了打算,没等结巴厨子开口就主动说:“饭还没吃完。”
“饭吃完了就出去。座位要给钱。”结巴厨子对此种谎言已经见惯不惊。
“知道了。”小伙子陪着笑脸。
我揣摩小伙子不知道座位要给钱,一定是打算二十元钱买盒饭,然后带着小孩坐着吃到天明。现在要补三十五,有些不划算,心里一定很矛盾,交还是不交。
结巴厨子给交了钱的人一瓶矿泉水和一盒香港产的咖啡,外加盒子里的几小包豌豆、胡豆和麦子做的干果。我感觉划算,多少也要值十元吧。那些长期在外跑的人认为,顶多值五元。餐车的管理者也算精明,怕乘客质疑餐车座位收钱的合理性,便以物换钱进行交易,一位愿打,一位愿挨,得以交易在供需双方各自的价值评估下进行。社会交易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不一会,小伙子的老婆进来了,一位整洁大方小巧机灵的重庆妹子。小伙子对她吩咐了些什么就让位出去了。
白衣结巴厨子来到重庆妹子身边:“掏……掏钱买啥?”
重庆妹子望着结巴厨子敏敏地笑,不急不慢地说:“急啥子。”
“他们叫我值班,我就得负责。我没那么多钱赔起。”
“一会买。”重庆妹子还是笑嘻嘻地说。
车厢里慢慢安静下来,突显那对年轻人的声音特别大。他们的对话直往耳朵里灌。时髦的女子对西装的男子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全国各地跑遍了,经销范围这么广,这么多客户,真是很佩服。”
男子没有被这句恭维话激动。仍是低沉谦虚地说:“没办法。逼出的。”
精灵的女子灼灼的眼神盯着男子:“你现在提多少成?”
沉稳的男子摇摇头:“不好开口,少得很,说起惭愧。”
“百分之十几吧?”女子瞪大眼睛期盼着迫不及待地追问。
“不到。”男子心不在焉地说。
“那是多少?”女子眼睛不放过男子的眼神,单刀直入,已没有了一点隐讳。
男子似乎产生了戒心,扭过头躲过女子的眼神,慢条斯理地说:“告诉你了,就没意思了。”
周立波秀:“中国人的不好意思就是好意思,没有意思就是有意思。”
那男子的“没意思”就是说“告诉你了,今夜就没有人陪我聊天了,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了,我的饭碗就让你端去了。”
中国人语言的魅力就在于此。
精明的女子似乎觉得上车后乃至上车前,从认识那一刻到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缺少了对话的原动力,慢慢地少了热情少了话。后来有人坐在了他们旁边,车厢里真的静了下来。
列车到了铜仁。餐车又拥进很多人,基本上一条座椅上坐了一人。白衣结巴厨子又开始收钱了。来到小孩熟睡的重庆妹子跟前:“买吗?”
“多少钱?”重庆妹子笑着故意问。
“三十五。”
“少点啥?刚才我们买了盒二十元的饭。给你十五?”
“不……不干。少了我要赔起。”
“那么二十。比一半还多了。”重庆妹子仍然笑着说。
“又不是做生意。他们叫我值班,我就要负责。”
重庆妹子交了三十五元钱说:“娃儿就不交了。”
“你们只能坐一个位子。”结巴厨子很坚持原则。
结巴厨子原地转过身,站在与重庆妹子对坐的一位正在聚精会神看报,头发花白的老者身边。他站着,老者坐着;他低头看着老者,老者埋头看着报。沉默许久,老者似旁若无人没任何反应,结巴厨子只好悄然离去了。我揣摩着此刻老者的心理。他心知肚明索要座位钱的人就站在身边,结巴厨子与重庆妹子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座位要付钱,又装着全神贯注看报什么也不知,故意不理会白衣结巴厨子。待结巴厨子主动问他付钱时,他才反击,有力地反击。他一定有充足的理由不付钱,或许只要白衣结巴厨子开口收钱,他就会毫不争辩地递上百元大钞,或是起身低头默默地走出餐车。我又揣摩着白衣结巴厨子的心理。他为什么不对老者开口?是碍于老者的厚重,还是碍于老者的威严?是对老者起了怜悯之心,还是觉得餐车座位收钱理亏?或许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此时此刻,双方心理的博弈考的是定力。老者花白的头发就已经在定力上占了上风,他埋头看报一言不发的坦然淡定彻底击垮了白衣结巴厨子的心理防线。
车厢里又安静下来。我缩卷着身子裹成一团,睡在仅有两人座位的座椅上,尽量使纷繁复杂的头脑静下来。
迷糊中,车又停了,到了秀山。感觉上了很多人,车厢里闹哄哄。结巴厨子高声地对睡觉的人喊:“起……起来!起来!”我装着没听见,想一人霸占两个座位躺着舒服些。结巴厨子来到我身边,用脚蹬蹬座椅:“起……起来!”我的定力没有老者好,赖不住了只好爬起来。
餐车的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人。老者站起身回头瞟了一眼餐车,默默地走到餐车进门的过道上。老者的眼神很深邃很平和。我真为老者担心,夜晚在挤满人的过道站着,这么远的路程,受的了吗?为三十五元钱把身子骨弄坏了,就糟糕了。看来像我年轻时把三十五元钱看得很重,大有人在。仍在为温饱而奔波的人不少啊,有多少人毕生就只做这件事!
靠着我坐的人,以及和他一起上车坐在我对面的两人。看上去很有钱,像在山沟里发了财的土老爷。一点不忌讳,一点不掩饰。当结巴厨子对他们说要付钱,他们一口应允。当知道一人交三十五,他们认为太便宜划得着。故意高声问:“有酒吗?”好似在像全车厢的人通报——我们喝酒了。
“有!”结巴厨子也提高了嗓门。
“是啤酒还是白酒?”
“啤酒。”
“多少钱一瓶?”
“五元。”
“真便宜。秀山最便宜的啤酒也卖四元钱一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说:“快快拿来!”大有梁山好汉大碗喝酒的豪气。
结巴厨子屁颠屁颠地跑到柜台,从橱窗抱来一箱剩余的液拉罐啤酒。原来啤酒是330毫升的罐装,不是他们理解的630毫升的瓶装,有点上当的感觉,话已出口不好收回,只得硬着头皮全部要了。一共十罐,五十元钱。付钱给结巴厨子时,结巴厨子改口了,激动得更结巴了:“六……六……六元一罐。”好费力才表达出了。三个男子感觉上当的火一下冒出来,大声对着车厢说:“你说五元钱一瓶,怎么几分钟就升成六元了,坑人也要坑在明里,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有意把话放出来,让全车厢的人都听到,包括坐在车厢卧铺一端的列车员,扫结巴厨子的皮。
结巴厨子自知理亏,没有争辩,收了五十元钱离开了。来到一位趴在桌上睡觉的小伙子身边:“要坐在这里吗?”
小伙子很不情愿地抬起头,恶凶凶地问:“啥子?”
“座位要付钱。”
小伙子爱理不理,看也不看结巴厨子一眼,慢慢地从胸前的内衣里掏出钱包,毫不隐蔽地当着大家的面把钱包打来,露出钱包里夹着的一大叠百元大钞:“多少钱?”
“三十五”
小伙子瞪大眼睛,顺手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理也不理结巴厨子,又趴在桌上装着睡起觉来。
结巴厨子似乎察觉了什么。又问:“票呢?”
小伙子又慢慢抬起头,恶凶凶地问:“啥子票?”
“火车票。”
“没有。”小伙子知道被盯上了瞒不过,很不情愿地回答。
结巴厨子很高兴,像立了大功,马上向列车长报告。
小伙子自认倒霉,为了挽回面子,拿出手机,大声地放起了电影。并把钱包从怀里摸出放在桌子上,似在告诉人们,我不是那种逃票的人,我有钱。
结巴厨子当着小伙子找了六十五元,没提补火车票的事,像把补火车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小伙子看得真切,把钱装进了钱包里,也不提补票的事,有种遇上结巴厨子这样记性好忘性大的人的窃喜。
我旁边的三个男子很海,高声叫嚷着结巴厨子送点下酒菜来。结巴厨子很兴奋,心里明白着呢,庆幸今天遇上了猪脑壳。跑过来哈腰赔笑:“餐车的卖完了,一会手推车推回来,就给你们送来。”
三个男子拉开液拉罐喝了起来,还大方地递给我一罐,我婉言谢绝了。酒后的男子想抽烟,碍着面子只好到车厢接头处去抽。想撒尿,没人的卧铺车厢厕所列车员不让进,只好挤到硬座的车厢去。他们心中愤愤地很不是滋味,像失了面子似的。
结巴厨子为今晚卖了很多钱而高兴,忘乎所以在车厢里抽起烟来,被三个喝酒的男子看见了。三个男子把结巴厨子叫到身边,没等结巴厨子开口,就一人点上了一支香烟,齐刷刷将烟雾向结巴厨子喷去。车厢里的瘾君子们也顾不了那么多,法不制众,抽起烟来,很快烟雾灌满了车厢。这是中国人的陋习,从众心态,只要有人带头,就会有人跟着做。不知此时西装革履抽烟的绅士们,心里是否受到公众道德的叩问。
三位男子很开心,虽然付了座位钱,买了高出超市价格一倍以上的液拉罐啤酒,但由他们带头打破了列车上的规矩,而且是在餐车上当着列车员的面。换来了心理上的平衡,扯平了,没吃亏,有一种胜利之感。
结巴厨子数着钱,反复清点座位上的人数,怎么就少一个座位的钱。挨着查票来到重庆妹子身边,才回豁过来。原来带着小孩睡觉的重庆妹子一张票占了两个座位。结巴厨子似抽了脊水,脑袋不够用,望着重庆妹子不说话,重庆妹子也笑着脸望着他,许久,他离开了。我突然感觉结巴厨子还没被铜锈侵蚀,还有同情之心。
火车轰隆轰隆摇晃着,车厢里又静了下了。餐车进门的过道上站满了人,车门已经关不上了。结巴厨子竭力维持着今晚由他管理的餐车秩序,不让站着的人迈进餐车的过道。
火车在一个小站又停了下来,上车的人不断往餐车拥,结巴厨子已经招架不住了,个别大胆的人站在了过道上。重庆妹子的男人在外面被挤得实在受不了,进来小两口抱着小孩坐在了一起。自觉地又付了三十五元钱。早知现在又何必当初呢!
过道的一位男子嚷着付钱买座位,结巴厨子不收钱了。旁边喝了酒的男子纵容道:“把钱塞给他,他收了你的钱就要安排座位,不然,就去坐他的位子。”男子真的把钱强行塞给结巴厨子,结巴厨子不收,就干脆把钱放在餐桌上,一屁股坐在了结巴厨子的旁边。邻座的列车员发话了:“不能坐,这是列车员的座位。”男子只好收起钱,回到了硬座车厢一侧的餐车门。
车厢里又进来了一位列车员,问结巴厨子:“哪位补票?”
结巴厨子把列车员带到小伙子身边。列车员对着小伙子说:“补票!”小伙子仍趴在桌上酣睡。结巴厨子拍拍小伙子肩膀,有些激动:“起……起来!补……补票!”
小伙子蓬松着眼,抬头望望列车员和结巴厨子,很不情愿地又从怀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哪里上的?”列车员问。
“前面。”
“前面哪里?”
“就是前面。”小伙子非常不满爱理不理地把头偏到一侧。
结巴厨子急忙补充说:“秀山。”
小伙子回过头,凶狠狠地瞪了结巴厨子一眼。
“多交三元五补票费。”列车员补充道。
“你随便收。你说了算。”小伙子铁青着脸极为不满地说。
列车员提醒道:“以后记住买票。”
小伙子已经失去了方寸,正在为偷鸡不成倒赊一把米而气愤。回答道:“我就不买。我愿意补票。怎么了。”说完就趴在了桌上。小伙子逃票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定恨透了列车员和结巴厨子。
外边的人小心地试着往餐车过道迈进,已经占了过道的四分之一。谁也不愿站在前面,站在前面就意味着首先被撵出去。他们很自觉,站着就不再移动脚步,很珍惜脚下这寸地盘。不说话,不抽烟,静静的,很担心自己的行为出格,惊动餐车的管理者被撵出去。
餐车挤进一位拉着箱子的少妇,戴着副金丝眼镜,旁若无人昂首挺胸时髦着呢。黑色的风衣随白色的围巾轻轻地飘逸,少妇特有的成熟风韵被浓烈的香味裹卷着,身后跟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老太步履阑珊,跟着少妇向卧铺车厢走去,被列车员拦下。少妇把箱子放在卧铺车厢一侧没有人的过道上,叫老太坐在箱子上,打定主意不走了,脱去风衣,丰满的身姿突现出来。结巴厨子迎上去,小心翼翼地说:“这……这……这里不能坐人。”
“挤死人了。我们买座位。”
“没有了。”结巴厨子说。
“反正我们不走了。老太太遭不住。”少妇理直气壮,把老太太推出来当挡箭牌。
贵人与贼民,高傲与卑微,在这餐车上被人们本质的需求扯平了。此刻,只有结巴厨子才是上帝!他有权安排座位,有权不准坐在过道上,更有权把看不顺眼的人撵出去。
座位上的一位女列车员对结巴厨子说:“就让他们坐吧。”
“那要补座位的钱。”结巴厨子一点不含糊地对少妇说。
“多少?”少妇问。
“七十。”
少妇二话没说,递上了一张百元大钞。
座位上的女列车员又发话了:“天快亮了,收一个人的吧。”
这时,餐车上的列车员只要离开餐车,就会有人来坐。结巴厨子只要一抬屁股,就会有另一个屁股坐下去。太挤了,太困了,站着的人可能早已支撑不住了。此时已是凌晨四点过,可能再没有人为交三十五元钱买个座位是否划算而纠结。餐车里的列车长、列车员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腾出的座位马上被抢占完。
女列车员友好地让老太太坐了她的座位。
喝了酒的三个男子兴奋得很,睡不着。与旁边的本地老乡吹起了薄熙来与汪洋的旧事,吹起了他与县长喝酒的事。那一天,和县长一行吃了一万多。“一万多”三个字说的特别重,有意突出那一餐的丰盛。喝了十瓶酒。“我拿给他三百三,他卖给我们三百八十五,一瓶酒转手就多五十五,真黑。”喝了酒的男子对酒店老板很不满意。嫌自己心太软,没把钱赚够,留给酒店老板赚钱的空间太大。“当喝到第十一瓶时,县长说是假酒。出门时,县长对着我说了句,明天你给我个解释。”酒后的男子反复强调“你给我个解释”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了,他是在告诉对方,他与县长走得很近,他是与县长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或是县长信得过的下属。旁边听话的人反复问:“你怎样给县长解释?又不关你的事,假酒又不是你拿的。”酒后的男子觉得对方没听懂,干脆直说:“怎么解释?简单得很。叫老板包个红包,认个错,不就了了。”道出了他办事的老道干练和与县长的亲近。
列车长从卧铺车厢出来,对着结巴厨子说了些什么。结巴厨子站在座椅上大声说:“要卧铺的,来列车长这里登记。早晨六点半,你们就离开餐车,餐车要卖早餐。”人们蜂拥而上,重庆小两口换了一张卧铺票,少妇带着的老太婆也买到了一张。车厢里的秩序被彻底打乱,混乱中,座位进行了重新组合。结巴厨子又开始收起钱来。旁边喝了酒的男子说:“这小子太狠,只能坐两个多小时了,还收别人三十五。”而此时此刻,就是这两个多小时的座位,拿着钱也买不到,站着打瞌睡的滋味你感受过吗。
秩序打乱了,过道里慢慢往前移动脚步的人已经占了过道的一半。结巴厨子已没有能力去维持,只好任其自然。站在过道里的人自觉维护着秩序,竭力挡住后面的人往前拥。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餐车与硬座车厢一样拥挤,他们就要被列车员赶出去。
餐车是卧铺车厢与硬座车厢之间的过渡,是吵杂与清静之间的衔接,是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的分界线,是一种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缓冲。
天麻麻亮,已是凌晨六点过。早起的餐车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坐着的人们趴在餐桌上酣睡。一想到还有半小时就要被赶出去,在连站的位子也没有的地方呆六个小时,心就发怯。又一想,这么多人,他们能熬,我也能熬。
清晨六点半过,餐车的服务员仍在忙着打扫卫生,酣睡的人们一点没有离开餐车的迹象。七点过,人们才开始慢慢醒来。昨晚,摆得很投机的那对年青人中的女子,提着香包到盥洗间去梳洗化妆,挤了半天也没挤出去,只好回来。
人们开始收拾行李,下一站就是重庆,下的人很多,都是忙着去办事的,当天还要返回呢,是说这列火车这么挤。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在乡下人的脑子中也在逐渐形成。
八点过,重庆站下了很多人,瞬刻间车厢里空荡荡。来到硬座车厢,一人坐了三个座位,当然是躺着的。舒适之余,感觉自己的肾功能特别好,要是昨夜在餐车里尿急尿频,才真是没办法。
昨夜坐在餐车里的人全部离开了,餐车恢复了平静。一位身穿旗袍双手放在胸前文静的姑娘站在柜台前,见我进门,慢慢地弯腰、细细地道声“早安”。结巴厨子已换上了整洁的白色上衣,戴着白色褶皱的圆形帽笔直地站在柜台旁的厨门前,与昨夜判若两人,让人产生了些许亲近感。拴着白色围腰脸蛋微红高挑的女服务员领口打着蝴蝶结,一枚孔雀发夹在头上高高挽起的富士山突闪突闪。
所有车窗白色绸缎的窗帘被服务员轻轻地慢慢拉开,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晨曦中的田野村庄被远山群峰追赶,像走马灯变着花样飞跑。座椅套上了白色的椅套,座位铺上了橘黄色的坐垫,窗前的餐桌铺上了洁白的桌布。一支郁丁香插在白色陶瓷小花瓶中,摆在靠近窗户的餐桌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瓶红色的香槟酒、一瓶黄色的威士忌、一只亮晶晶的高脚玻璃杯、一块桃色的餐巾布、两张叠成三角形的黄色餐巾纸,像郁丁香一样浓烈芬芳。又烘托出来此消费的人的高雅,还原了我没钱进餐车时清纯美好的向往。
我不愿打破餐车里华丽高雅的氛围,甚至吝惜坐下去破坏了餐车此刻的宁静,想把这幅完整的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记忆里。
二零一三年四月